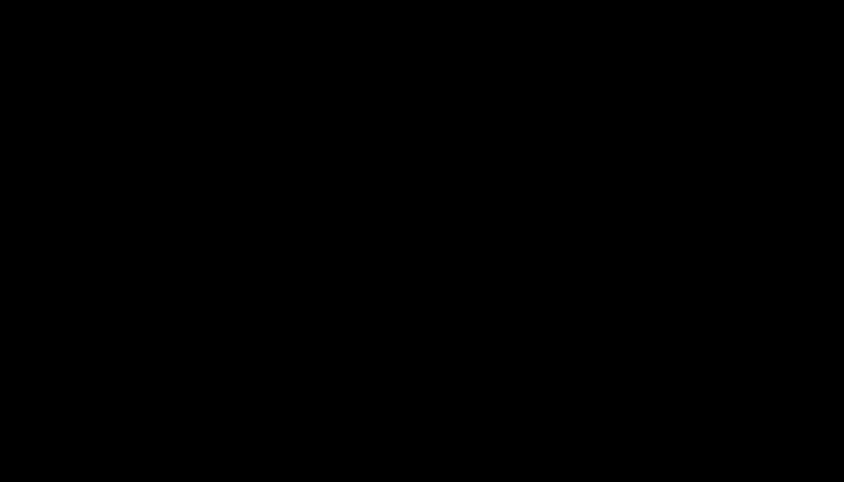
從「精準」到「表達」──臺灣馬戲與雜技身體訓練的多重面向
任何藝術表達都離不開特定類型的技術,特別是在表演藝術中,表演者的身體能力往往成為欣賞的基礎,無論是戲劇使用聲音與身體來進行扮演,演奏者對於器樂、聲響構成的掌握,還是舞蹈在身體節奏、力度與空間的探索。馬戲與雜技的表演項目、身體技巧紛雜,如果在某個程度上能被視為為一種藝術類型的話,大概我們都能同意這種它在本質上具有的混種性。
雜技與馬戲從「表演」邁向「創作」的光譜上,「技術」不再只限於純粹展現「超常難能」的技藝或身體技巧的招式,也包括如何「用身體技術進行表達」。來自不同背景的馬戲表演者在嘗試創作時,往往會發現過去的訓練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跡,影響或甚至限制了創作的發展,進一步有意識地去發展自己的創作路徑。本期主題專文試圖梳理近年臺灣馬戲表演與創作發展上,在不同時空場域產生的身體訓練及背後的思維,彼此之間如何針鋒相對或交互影響。
文字|余岱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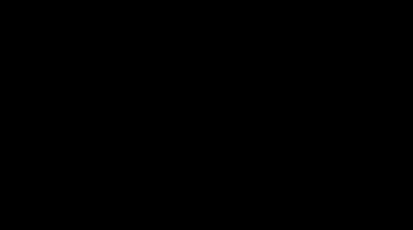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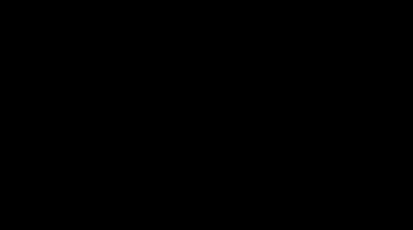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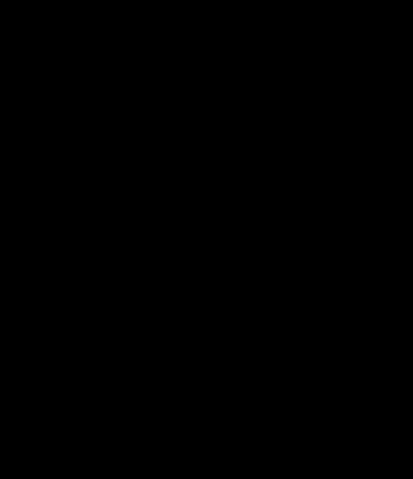
審美差異下的身體樣態:學院、比賽、選秀節目、街頭表演
臺灣特技、雜技與民俗技藝在學院中的身體訓練,承襲的是中國雜技文化傳統,在「技藝傳承」的基礎之上,和許多傳統技藝(例如傳統工藝或是傳統戲曲)一樣,有著歷時許久的審美標準。這樣的制式標準,有時和技巧水平有關,有時和特定的姿勢、表演符號或身體細節有關。這些標準可能是椅子要疊幾張、球要丟幾顆,可能是倒立時要將腳掌背繃直,或是結束表演招式後的引起觀眾鼓掌的亮相手勢與姿態。
在民俗體育受到教育政策支持的背景下,雖然多年來也有不同的演變,馬戲、雜技的比賽在臺灣並不少見。比賽在本質上雖然也帶有交流的性質,但基本上都有明確的標準,要完成特定的招式項目才能得分或獲勝,比起藝術競賽而言,更像是一種體育競賽。臺灣特技團的現任團員李軍回想高中求學時的身體訓練時就表示,當時的訓練方式,「比較偏向增進運動員的身體能力,例如柔軟度或爆發力(……)用運動員的邏輯和訓練方法來訓練演員的身體。」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副團長陳冠廷也表示,比賽的目標很明確,比的就是誰比較厲害,或是在沒有特定標準的情況下,誰讓大家覺得比較厲害。後者的描述,也適用於像「釘孤枝熱血大亂鬥」這樣更具交流性質的比賽活動中。
而從早年的綜藝節目到近年帶有競賽架構的選秀節目(例如「中國達人秀」或「亞洲達人秀」),其實也不乏特技表演者的身影。比賽除了技巧的展示與堆疊,似乎也會帶出不同的表演狀態。陳冠廷就表示:「常比賽的人有另一個優勢,就是臺風會不一樣,無論他會不會表演。」而馬戲創作者楊世豪回想在學時參與校內金獎比賽時也表示,除了關注身體技巧的高超程度,自己當時的身體也有展現出不同的狀態,但距離創作的身體還有一段距離。而在選秀節目中,通常入選者都能掌握一定程度的技巧,因此可能更著重製作單位要求的節目效果或表演氛圍。「當時我在節目上,或在街頭表演上,我注重的是情緒和氛圍所呈現出來的身體樣態」楊世豪表示,「你可以看到身體不太一樣,我不會說那是在演戲,只是覺得這樣做很舒服,那個選擇可能是一些很奇怪的舉動,後來發現當我開始做出「摸地板、撫摸大環、凝視大環」的舉動時,都是比較直覺的表演身體反應,但只表現在表面上,沒有深入到本質。」
除了比賽帶來的制式架構,看來自由、開放的街頭空間,也可能讓表演落入另一種機械式的循環中。近年專注公共空間展演的黃子溢,是先學了魔術後才自學踏入雜耍的領域。過去為了在街頭賺取收入,不但發展出自己的雜耍耐力訓練方法,也架構出一套演出的標準流程。他也表示這種訓練更像是運動員,而非創作思考,因為「當時有必需活下來的壓力,不然真的會餓死」。而他那套有著「標準流程」的街頭演出,最多一天可以演到二十場,「用現在的思維想,那時比較像是機器(……)很像進入工業時代,從發散行為到工業行為,一切都是為了有產值。(……)我可能腦袋在想著回家要吃什麼,但身體在做那些很精準的表演」

創作場域中,轉化身體思維的挑戰
經歷這些不同場域、審美標準和目標的身體樣態,近年許多雜技、馬戲表演者踏上創作的道路,甚至早在學校時就開始嘗試。有些人靠著自學摸索出可行的方法,有人則是大量接觸不同的身體訓練作為創作的基礎。
李軍和陳冠廷都不約而同提到學生時期嘗試突破「標準技術」的限制時,遭遇的困境。因為創新的身體語彙需要反覆實驗、驗證效果的過程,在以技藝傳承為主的教育環境下,更著重於表演的正確,嘗試創新的過程也會「打結」。這種看似矛盾的「習得技術──挑戰創新」對立關係,在藝術創作中並非什麼新鮮事,但在馬戲和特技表演的領域裡,這樣的衝突張力的確更大。不僅是因為馬戲動作常有一定的危險,也是因為新發展的動作成為身體語彙的過程中,牽涉到表演者和表演傳統以及同時代的觀眾如何進行對話,在「技藝」的架構中,更需要表演者自尋出路。陳冠廷這麼描述過去的學習經驗如何影響了創作的心理狀態:「以前嘗試一些東西會覺得很有趣,但可能技術不到位,或是在老師眼中不一定有趣,在練習或編排考試節目的過程中可能就被打槍。雖然我現在還在創作,但我相信在那個過程中信心也被打擊,因為以前你喜歡的東西,以及那些第一次想出來的東西,在當時都是被不認同的。」
即將前往圖盧茲馬戲藝術中心求學,正就讀比利時高等馬戲學校的舒建宏,比較臺灣和歐洲馬戲教育的訓練方法時表示,臺灣的肢體訓練項目多元,比較追求原本該項目的美學標準,例如特技的標準,現代舞的標準。李軍也表示臺灣特技教育的身體訓練很全面,讓學生在未來發展的方向有更多選擇,但「缺點就是好像什麼都會,但什麼都不精」。在比利時,由於馬戲文化為大眾所熟知,教育機構中即便是教導舞蹈、戲劇的老師,也會運用不同的方法讓馬戲表演者吸收、轉化不同的身體技巧,成為構思馬戲創作的方法之一,而不是學習特定的舞蹈技巧或戲劇表演方法。
在學院體系之外,臺灣其實也有非常豐富的身體表演進修資源,但如何將不同的身體方法轉化到實際創作,就更看個人吸收與消化的能力。沒有受過正規特技教育的黃子溢,在街頭表演的領域嶄露頭角數年後,自2017年開始「分清楚表演和創作」的差別,並且在參訪日本、韓國及歐洲各地相關的藝術節慶後受到許多刺激,開始大量接觸戲劇、喜劇、肢體表演、舞蹈的工作坊,他表示上的課程多到「周圍的人開始無法標籤自己」,同時,對於創作黃子溢也很節制,一直到2020年才開始將多年累積的能量慢慢展露出來。
身為獨立的表演工作者,黃子溢認為要跨出原本的環境,去學習其他事物其實非常困難,信念是其中的關鍵:「你得相信前方會有路,才有辦法去走。如果你沒有真的參與這些訓練,你就不會相信這件事。我覺得創作也是。相信的力量在創作和訓練的過程中蠻重要的。這其實是想回應比賽,因為比賽就是一翻兩瞪眼(……)這有點批判,但我認為要去相信進行一堆表演肢體訓練對創作有幫助,對臺灣教育體制下的小孩來說很困難。創作不是立刻會得到回饋的一件事,例如可以賣到多少錢,可以有多少人買單,但你會得到心靈上、靈魂上的滿足。這樣的行為和競技有蠻大的對比。」
另一位創作者楊世豪也認為,他在創作上是接觸了許多工作坊,特別是歐洲的馬戲工作坊後,才開始注意到身體,也是做了《拆解馬戲表演者的身體語彙──其一:與編舞家》後,才有更深的體悟。他表示:「我以前不懂馬戲身體語彙是什麼。我現在才了解它不是演一演戲,再搭配技術就是馬戲身體語彙。而是從道具本身長出來,身體有一些訊息和符號出現,那才是馬戲的身體語彙。我認為這是當代馬戲很重要的一把鑰匙。(……)用馬戲的身體技術去回應你在乎、你想傳遞的訊息、你想了解的,這些過程要怎麼讓它視覺化……在我畢業剛進入社會時,這些我都沒有注意到。」
從這些過去接受「標準技術」學院訓練,或是高效率街頭表演環境出身的馬戲創作者口中,我們觀察到他們開始意識到,也回看不同表演場域及身體訓練帶有的審美機制,進而尋找身體回到創作時在表述上的更多可能,發展不同於以往的身體語彙。在有限的篇幅內,希望本文能作為理解臺灣馬戲身體訓練的其中一種觀點,甚至成為未來臺灣馬戲表演推展身體論述的起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