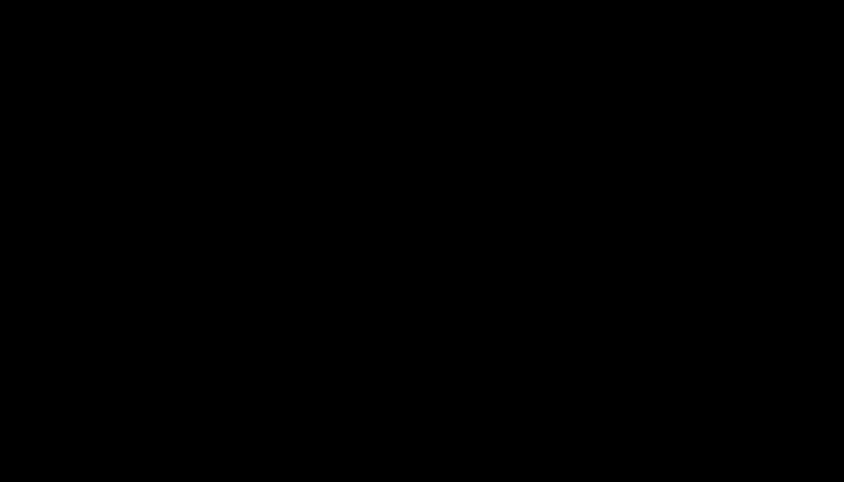
【編輯筆記】
女性表演者在馬戲中一直是少數,也常被限定於特定的表演項目或位置,例如高空、軟骨功。這個現象不只存在於臺灣,也是世界上普遍的現況,背後的文化與社會原因十分複雜。
2020年創造焦點製作全女性的馬戲作品《#Since1994》,賦予臺灣雜技及馬戲的女性表演者們幾乎未曾現身的立體形象。這兩期的話馬戲,我們總共訪談六位女性馬戲工作者,讓他們的觀點在紙上相互對話,也彼此激盪。
梅芷菱
你和雜技/馬戲的第一次接觸?
大概十歲時,我看到就讀民俗技藝系的哥哥倒立,從此打開了我的世界觀:人怎麼可以倒過來?我就跟爸爸說一定要讀這間學校。一開始家裡有一些刻板印象,覺得女生學這個太辛苦,但在我的堅持下還是同意了。在學校,老師常把我們兄妹拿來比較,但我很倔強,不服輸。當時學校對於表演項目也有刻板印象,覺得女生不需要練倒立,但我很堅持要學,連老師想把我趕走,我都自己在旁邊偷偷學。
對你來說雜技/馬戲是甚麼?
在不同的階段,馬戲對我來說都有不同的意義,綜合來說,馬戲很像童話故事裡的冒險。身體的冒險、物件的冒險,和夥伴共同歷經挫折和痛苦後的成果。大學時,我發現很多很厲害的學姊,畢業後都不做馬戲了。也觀察到當時藝術節或演出邀請嘉賓都是男性,我就萌生了一種使命感,想要在未來把一群很厲害的女生聚在一起,做一個很酷的表演。開始做女馬後,我真的確定了自己對馬戲的使命感。我想要為臺灣的女性馬戲工作者創造一個平台,撕掉刻板印象的標籤,讓我們不再只是花瓶、陪襯,而是說自己故事的創作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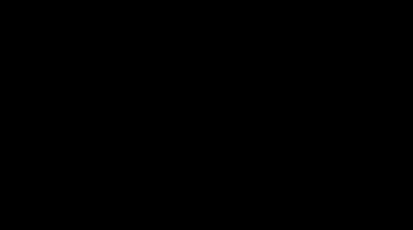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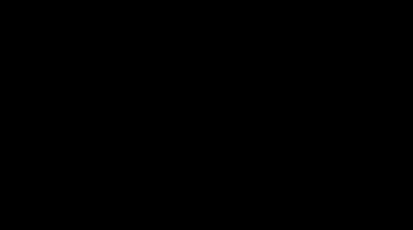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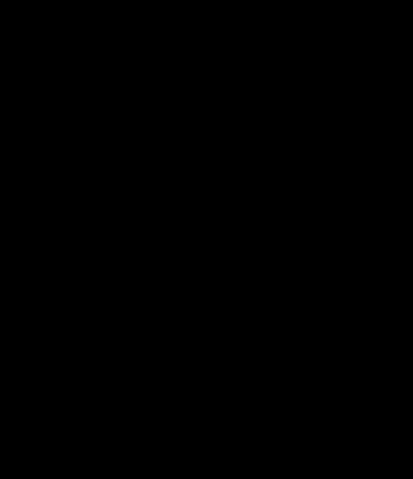
江侑倫
你和雜技/馬戲的第一次接觸?
第一次接觸馬戲是2006年的兩廳院廣場藝術節,星合帶我去看七手指特技劇場的演出,在那之前我其實不知道馬戲是甚麼,只知道大概跟動物表演有關,本來以為會是個很盛大的馬戲表演。七手指演出規模並不大,但創造了很大的想像空間。那個演出空間是個小小的帳篷,內容也不是甚麼奇幻故事,而是一般人的形象,從冰箱走出來發生的故事。但當時我並沒有覺得要在馬戲領域工作。
對你來說雜技/馬戲是甚麼?
馬戲是自由和不自由融合在一起的象徵。我發現馬戲需要透過很嚴謹的訓練,像是一種限制或不自由,去創造出更自由的畫面與想像。我把馬戲當作我工作的元素之一,用這個元素去做更多事情,不管是出版品、平面設計、裝置等等。馬戲對我來說是個切入點,讓我意識到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。馬戲對我來說也像是一個出發點,它也提供了一種精神,讓我覺得:不管要做任何計畫,都沒有什麼不可能,就算會面臨一些風險,也覺得應該是做得到的,因為接觸馬戲讓我發現我有更多勇氣面對挑戰。
張欣怡
你和雜技/馬戲的第一次接觸?
第一次看馬戲大概是民國七十到八十年間,有很多傳統馬戲團來臺演出,進帳篷、有大象的那種,也在電視上看過李棠華特技團。2005年我參訪法國時看了第一個當代馬戲作品──Johann Le Guillerm的演出。當時非常震驚,因為跟兒時記憶和想像中的馬戲都非常不同。他的物件表演除了畫面、技巧,也蘊含了科學和哲學,在那之前,我不曾想過劇場或議題性的表演可以透過當代馬戲來詮釋。
對你來說雜技/馬戲是甚麼?
我覺得馬戲是一種總體藝術。很多馬戲表演者都很斜槓,例如有些人也是科學研究者。我看到的當代馬戲彷彿體現了早期藝術尚未分類的狀態,不是純戲劇、純音樂,而是融會貫通所有材料和工具後呈現出的結果。馬戲到今天都還有很強、很深厚的動能,不斷引起好奇的原因之一就是,馬戲不僅展現人超越極限的能力,也展現了人如何把各種看似分開的技術融會得宜。在當代馬戲表演裡,每個演出都可以帶給我不同的體驗,那種體驗很全面,不只是聽覺、視覺,也有思考,也有感官上的刺激或挑戰。

梅芷菱
馬戲藝術工作者,專長高空特技。近年研究如何利用馬戲獨特的身體語彙,探索性別意識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連結,2020推出以「女性」為核心的作品《女馬系列#Since1994》,未來將發展為平台式計畫。
攝影:吳伽莉
江侑倫
南投人,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。擅以各種角色參與計畫,於2016年與陳星合共同創辦星合有限公司,致力於臺灣馬戲拓展,透過舞蹈與劇場養成經驗,賦予馬戲更多風貌,以供多樣想像。
攝影:洪佩瑜
張欣怡
2021衛武營馬戲平台策展人 。現旅居盧森堡,透過書寫、觀察和對話,持續關注國際馬戲及舞蹈創作之趨勢發展。曾於2017-2021擔任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節目部國際事務組長。
攝影:Sara Lando
採訪、整理|余岱融